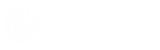We Fought Over The Moon
《We Fought Over The Moon》的音乐充满了表情,或者说,语气。它有时是单纯欢乐的,有时充满紧张感,还有吃力、濒临昏迷,以及无所顾忌地忘记外部世界而潜入自身内部发出的怪异、不和谐,还有窒息中露出的一丝诡异。在《I! Alarm! Alive! Alive!》中,潜意识和现实彼此穿梭交融,让人难于区分,睡梦般的音乐伴随着此起彼伏涌现的情绪,在这些情绪中时常又因自我出离而产生了自我观看,就像意识到自己在做梦的梦境,唱腔的丰富多变也标示着梦呓的丰富表情。这些当然应该部分地归因于制作人Angus Andrew的加入,这张专辑中有一些单曲基于最初的排练或演出版本有了较大的改动,就像我们在《Last Days of Louis XIV》中听到的那样,它的结构得到了调整,伴奏部分出现了许多急停和骤起的对比,同时,音乐与人声的前后关系也更加自由地游移,彼此掩映。 这些润色为歌曲营造了戏剧性的氛围,相应地,人声的层次处理也更为立体了。这些在听觉与文本之间的关系方面制造了某种复杂性——音乐、人声、情感逻辑这三者之间不再是简单的对应、叠加,不再是同一频率的曲线重叠和平滑推进,而是如整张专辑的情绪一样此起彼伏充,满了自我分析、对抗,还有暧昧。从《快快》开始的最后四首歌,就文本而言它们显然走向了一个下沉的、充满不祥之兆的通道,或许这仅仅是录音的先后顺序,而并不意味着更多,好在最后一首《Last Days of Louis XIV》在音乐上的丰富和叙事性标题(这在专辑中显得很突出的)对本文的下沉做出了平衡,它是否隐约指出了一种新的方向,走向一种可称之为“客观的主观性”的创作? 这张专辑相比文隽此前的乐队“怪力”,它的内部结构变得更为复杂——更加专注于内在结构的丰富体验,不论在音乐还是情感两方面都是如此。但是在遭遇音乐时完全不必依赖分析的态度,事实上,它要求我们与创作者一样投入情感,它在根本上依然是一个简单而纯粹的邀请,邀请我们共情并且在自身的生命实践中更多地以情感的方式构建我们与世界、与他人、与自己的关系。